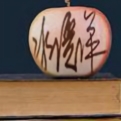南陽的明山路,像一條被歲月反復(fù)揉搓的麻繩,早起了褶皺,黃昏又勒進(jìn)新痕。
八十六歲的老先生和八十三歲的老太太,每天在這條麻繩上打著結(jié)——凌晨四點(diǎn)一個(gè),夜里十點(diǎn)一個(gè)。
他們第一次打結(jié),是1958年。
祖屋還在麥浪盡頭,青瓦上蹲著一只瘦貓。20歲的丈夫把鋤頭扛成月牙,18歲的妻子把炊煙系成辮子,兩人把名字寫進(jìn)生產(chǎn)隊(duì)的工分簿,也把自己寫進(jìn)南陽的泥土。
第二次打結(jié),是1992年。
城市像饑餓的巨獸,一口口吞掉菜畦。一夜之間,油菜花的金黃變成塔吊的長(zhǎng)影。夫妻兩口的竹籃里,還躺著沒賣完的菠菜,腳下卻簽下了征地協(xié)議。四套房,每畝地九百八十塊,他們按手印時(shí),像在給一個(gè)時(shí)代畫押。
第三次打結(jié),是2003年。
沒有編制的橘黃色馬甲,套住了兩件洗得發(fā)白的毛衣。明山路三百米,掃帚是延長(zhǎng)的手臂,簸箕是隨身攜帶的月亮。工資從三百五漲到八百,再漲到一千二,卻在某天突然停表——“年紀(jì)大了,回家吧?!?/span>
那天,老先生把掃帚靠在南國(guó)玉蘭樹下,像把老伙計(jì)托付給風(fēng)。
如今,他們?cè)趦蓚€(gè)兒子家輪流住,像兩只被孝順的候鳥。
可候鳥每天仍要飛——凌晨四點(diǎn),飛進(jìn)小區(qū)的垃圾桶;晚上八點(diǎn),飛回明山路的燈影。紙箱、塑料瓶、生銹的易拉罐,是他們撿到的云朵,稱重后,換成一把小蔥、半斤豆腐、偶爾加半只燒雞。
我問:“苦嗎?”
老太太把癟嘴笑成一朵山菊:“苦啥?走路就是吃補(bǔ)藥,翻垃圾桶就是翻寶盒。”
老先生補(bǔ)一句:“政府給發(fā)每人不足二百元養(yǎng)老金,兒子給添米面油,我們掙的是零花,更是勁頭。”
黃昏十點(diǎn),我陪他們走最后一趟。
大街上的梧桐把路燈掰成碎金,灑在兩個(gè)佝僂的背上。老先生忽然停下,用鉗子撥拉一只空易拉罐,罐身映出他彎曲的倒影,像一枚被歲月壓彎的月亮。
“你看,”他說,“它還能站直?!?/span>
說完,把罐子踩扁,丟進(jìn)蛇皮袋,發(fā)出清脆的“咔嗒”——像給這條麻繩,又打了一個(gè)新的結(jié)。
回身望去,那條路綴滿他們打的結(jié):
凌晨的結(jié)是黑的,卻拴住第一縷晨光;
夜里的結(jié)是亮的,卻系住最后一粒星子。
這些結(jié),終將松開,被風(fēng)、被雨、被后來者的腳步碾平。
但此刻,它們牢牢系住一對(duì)八十多歲的老人,也系住南陽的黎明與黃昏——
讓一條普通的大街,有了不肯老去的脈搏。